杏花
我生在小城。小时候觉得小城好大,稍大点就不觉得了。在大点,大概就是15岁吧,我离开了小城,那之后的小城在我的眼里已经很小很小了。
我家有一棵杏树。据说是自己冒出来的,算年龄比我还大一岁。每年三四月,杏花就开的纷纷扬扬的,有一年花色偏白,又有一年花色偏粉。快到清明的时候就谢了。
杏花谢的时候比开的时候好看。花开的时候是一朵一朵开,就在光秃秃的树枝上,还没有叶子,花又小几乎看不见。花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,一树一树的,和下雪一样。远远望去就像树上起了一树烟。
“ 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我小学时候学这诗,那时候觉得老师讲错了。牧童可能还在牛背上吹笛子呢,怎么能告诉诗人什么地方有酒呢。牧童吹着一首呜呜咽咽的曲子,诗人问他:“小哥,多有启动,这地方哪有酒家?”
牧童还只是吹着笛子,用手指了远方,诗人顺着手的方向看到一个开满杏花的小村庄。我觉得这首诗应该是这样的,只是呜呜咽咽曲子里的雨天杏花总让人想起离别,到底有点凄凉。
我家还有桃树、梨树。桃树比杏树矮,桃花比杏花娇艳,桃子也比杏子好吃。可我家的桃树却早早枯死了。梨树是母亲种的,好多年都不开花。第一次开花的时候我已经念初中了,好像也是两三月,只开了几朵。后来结了梨子,那梨子吃着甜,却长的难看。
一
学前班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小池塘,里面有好多芦苇。我以为世上除了我谁也不知道,每天放学后,我就去那里抓蜗牛,养在玻璃瓶里。后来有一天早晨,蜗牛都只剩下壳。
我小时候很孤僻,小玉是我第一个朋友。我们两个找了一块田地专门写家庭作业,上了初中后我就不愿在和她往来,因为她成了好学生,而我是差生;对此她似乎不明白,见我若即若离几次后也不再同我往来,这样一下就过了十几年,我偶尔会梦起小玉,清梦聊聊,始终不安!
二
我小时候最喜欢拿小铲子在花园里挖洞。我总想着如果我有一把特质的小铲子,会快乐很多!
小城
一
我家在城东大街,离城中心不远。
小时候小城里种满了白杨树。树多鸟就多。乌鸦的叫声有点像老女人的笑声,母亲把乌鸦叫“野呱呱”,还说她们小时候听见乌鸦叫就会喊“把盐拿来,吃野呱呱肉”,这样乌鸦就会害怕飞走。
小孩子才不信这一套,也没人把乌鸦叫野呱呱。小男孩人手一个弹弓,到处打鸟打老鼠。弹弓高手能一弹弓打掉小鸟的头。
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乌鸦,只听过它叫。也没见过黄鼠狼,蝙蝠,萤火虫。同学们说这些都很常见,他们中有人还抓过蝙蝠。说那蝙蝠飞进他们家,倒挂在他们家门背后,长的和老鼠似的,他一把就抓住了。
我没有这样的奇遇,我家里只来过老鼠。不过有一年冬天,我拿着小铲子在院里挖坑,挖出了一只红色的青蛙。
我最喜欢秋天的田野。农民把田里的粮食收干净,秋高气爽,不热也不凉。我和小玉放学后就跑到田野里,我们坐在田垄上写作业。这样写作业会快一点。写完后就坐在田野上听鸟叫。
小玉是个干净孩子,她在田垄上放一个厚点的纸板,纸板上面在再放一层塑料,塑料上面还要放一张纸,最后才坐在上面。她也给我准备了这样的坐垫。
有一次,我们在田野发现一只会说话的八哥。八哥飞的很低,我们追着它跑了好久。
快到冬天的时候,田里还有浇一次水,俗称浇冬水。到冬天了,田里的水就变成厚厚的一层冰,田野也就变成孩子们的溜冰场。小男孩都有自己的小冰车。通常都是两个人一组玩,一个小孩在前面拉,另外一个小孩就坐在后面吆喝。滑不了多长时间,孩子们就摔成一片,大家都躺着笑。
我们女孩没有冰车,就一个站着一个蹲着,站着的拉着蹲着的跑。
虽然大家都在一块田里滑冰,但男孩不找女孩玩,女孩也不愿意和男孩玩。
二
城南大街就比较繁华了。
邮政局、新华书店都在那一片;卖花卖鱼的也聚在那。
每到周末我就去邮政局看窗口里新出的明信片,然后去新华书店蹭故事书看。新华书店里大多都是辅导书,故事书很少。要看故事书就要去图书馆,可图书馆总是不开门。到晚上六七点,图书馆门口就架起电视音响,一帮四五十岁的人唱卡拉OK。
我母亲有两个朋友在城南开批发商店。一个姓吴,是个两百斤的胖子;另外一个姓杜,脸被太阳晒的黑黑的。她们什么都卖:床品、零食、文具、还有服装。她们的小孩年纪一样大,又在同一个学校上学,每天早上约着一起上学,早点就在自己店里拿,什么方便面、辣条,面包,蛋糕应有尽有。有时候你拿我家的,有时候我拿你家的。后来两家孩子吵架,两家的大人就提说起这事,胖吴阿姨说杜家的孩子鸡贼,尽拿自己家的方便面。小杜阿姨一听就气的头发直竖,反驳说自己家店里的铅笔、转笔刀你家孩子也没少拿。胖吴阿姨听小杜阿姨这么说更是气的面目通红,浑身冒汗,还说小杜家孩子鸡贼,都是因为大人就不厚道,同样的货,他们就贱价卖,掺行(破坏行规)。这样闹了一回,两边的孩子也不一起玩了,大人更是几十年没说过话了。
三、城隍庙
小城中心有座钟鼓楼,鼓楼后面是个戏台子。平时没什么人去,也没有唱戏的,总是冷冷清清。到了正月十五,那才热闹。
鼓楼上有卖字画的,卖灯笼的;还有猜谜语赢奖品的。到了晚上还放烟花,刚开始放的那几年,大家都挤在城中心看,好像城市开在烟花里一样。后来有孩子挤丢的,有腿脚不利索被游人踩死的。慢慢的,也就不挤在一起看了。
戏台子下面有卖元宵的,卖酿皮的,还有卖鱼苗子的。有时候戏正看到好处,忽然来了一群舞狮子的。这边小青要杀许仙,眼瞅就要拔剑了;那边母狮子要生小狮子,两边都急着,想跑根本就挤不出去。只好张着一双眼睛来回看。
看完戏,就要去城隍庙烧香。城隍庙人更多,隍庙后是个小学校,里面也搭个戏台子,年年都举办卡拉OK。
据说城隍爷生前是位将军,似乎叫什么“定远将军”。我们这城隍爷可新潮呢,前几年听守庙的说城隍爷和城隍奶奶要离婚,闹了几个月,到底没离成。城隍奶奶答应城隍爷纳妾这事才算完了,不信,看罢,偏殿里还有小奶奶的席梦思哩。
后来,人们拜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时候,都顺便看看偏殿里小奶奶的席梦思。
四、夜市
夜市,简言之就是摆地摊的和逛地摊的。逛地摊的一般称呼摆地摊的“老板”;摆地摊的互相之间叫“街油子”。
夜市每天下午六点开始,有的时候是7点。四点的的时候摆地摊的就要去抢地方。小城里摆地摊的大多都是中年妇女。年轻的女孩害怕被街上的流氓调戏,宁可在田里种菜。年老的,话也说不清楚,路也走不稳当,是更不可能摆地摊了。
摆地摊的女人大多是离过婚的,娘家也靠不住,没有工作的。也有的离婚的时候拼死拼活的要了孩子的。她们走投无路了,就出来摆地摊,卖袜子,内衣裤,和小孩的衣服维持生计。至于没有离的,虽然还有男人,却更加不幸。
摆地摊经常为抢地方吵架、打架。通常吵架吵不了几句就被周围的人劝开;打架也不过几分钟完了;说是打架,其实就是相互挠脸,一场下来,脸抓的花猫似的。
打完没几分钟夜市就开始了,通常东西还没卖出一件,上税的就来了。这种情况下,十有八九是要逃税的,其实也不是逃,顶多是让上税的多等一会,开张了就交税。交完税不一会,流氓就来了,她们没什么钱,就送些袜子,手套之类的。
夜市一开始,她们就忙的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她们反应敏捷,小小的摊位,有的人问袜子什么价钱,有的人问内衣什么价钱,七嘴八舌的围着一群人,她们都应付自如。
其实卖这样的小东西是很难发财。要发财就要卖便宜货,卖价便宜,进价更便宜。说明白点就是假货。比如秋衣秋裤,我们那里叫线衣线裤,15块一套 ,不退不换,不讲价钱,老板再吆喝几句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”,那么老板也很快就发财了。
但发财了也没有用,一来钱财不长久,一时发了,一时就赔了;二来,钱财并不能让她轻松一些。她是女人,没了男人就有许多力气活干不了,只好陪笑脸请人。
有男人的也好 不了多少,家里电线起火了,男人看了一眼居然哼着小调出门找人下象棋。下够了,玩好了,回家了,看见她乱着拧电线,换保险丝还没做饭,就气不打一出来:这时候还不做饭,想饿死我吗?于是又拍板凳,砸桌子开始吵架。
夜市都是凌晨一两点结束,这时候她们就围在一起家长里短的寒暄,有老公就说老公怎么体贴自己;有孩子的就说孩子学习多么好,怎么懂事,老师怎样器重;没老公没孩子的就说有多少男人追求自己。
等到街上确实没人了,她们才收摊回家。回到家腿也硬,背也硬。肚子饿了,烧点开水,开水就馒头。吃饱洗漱完了,有孩子的还要洗衣服,孩子的衣服脏了,穿到班里同学要笑话,老师也看不不起。
后来。
她们都老了。
她们喜欢和老伙伴们聊天。听着别人的家庭,别人的孩子,别人的一生。很快的,她们的一生和别人的一生重合了。她们看到年轻人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,看到别人的家庭就想到自己的家庭,看到别人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孩子。那些年,那些事,那些人都仿佛一个个钉子,钉住她们的手脚,她们如同圣子,如同罪人。
相关推荐:
《故乡系列专题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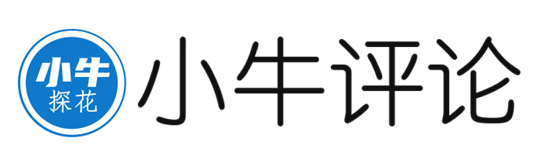

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