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万事开头难”,确实如此。我一直都想把自己离奇的经历讲给人听,又怕别人听了笑话,说我胡编乱造、瞎扯淡,就只能多年来憋在心里。可人总有憋不住的时候,电视里也经常说,“只有死人是不会说话的——”,我可不想把这些故事带进坟墓。
也罢,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。
文/笙歌破晓
我出生于80年代,与周围同龄人相比,我性格安静,话不多,显得老成,一直是大人们眼里的“乖孩子”。小时候,我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,能准确地说出大人们已经遗忘很久的事情具体细节,而我与其他孩子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,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、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,尤其是我的耳朵,异常灵敏,能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——如果您信,那么后面的就是我真实的经历;如果不信,就当是一篇灵异故事吧。
画中邪魅
我三岁那年,母亲在一所乡镇卫生院当护士,经常值夜班,父亲又经常出差。我家就住在卫生院办公楼一楼,二楼是行政办公区和病房,也是我母亲值夜班的地方。母亲值夜班的时候,就是我最难熬的时候,我害怕孤独,总是离不开母亲温暖的怀抱,又深受着无尽黑夜的折磨。
一天夜里,我在床上碾转反侧,一个女人的歌声将我吵醒,那声音婉转幽长,清脆刺耳,时远时近,渐渐地靠近我耳边,震得耳膜欲裂。突然,一阵寒气袭来,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,感觉手指甲扎进了皮肉,脖根处刺痛,呼吸困难。我睁开眼向下一看,一只惨白、纤细的手,正掐在我的脖子上,长长的黑指甲。我吓懵了,觉得全身发冷,顿时额头冒汗,猛地向上一看,看到了一张女人的脸。
在月光的映射下,那是一张像涂过白粉的瓜子脸、血红的嘴唇,冲着我冷笑,一头乌黑搭肩的卷发,那只手的力道越来越大,那张脸变得狰狞、扭曲——啊——我吓得大叫,哇的一声,哭了起来,哭着、哭着,听到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我听出来是母亲回来了,紧接着是钥匙扭动开锁的声音,咣当一声,门开了,灯亮了。
“狗娃,你怎么了?”母亲走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我的额头,用手绢擦去我额头上的汗珠,我还是哭个不停。母亲坐到床上,把我抱着靠在怀里,温柔地问我,“是不是又做恶梦了?”我抽泣着答道,“有个——女人——掐我——脖子。”“在哪里?”我指床右侧对面的墙壁说,“刚刚——还在,你一回来——她就——钻到墙里了。”母亲以为我做恶梦了,不相信我说的,把我哄睡着,又去值夜班了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母亲已经做好饭喊我了,我盯着床右侧对面的墙壁,墙上贴着一副油画,那油画上的女人身材高挑,穿着黑色的旗袍。再仔细一看,雪白的瓜子脸、血红的嘴唇,黑色过肩的卷发,两只白皙的手,长长的指甲,左手放在胸口,右手拿着麦克风。除了指甲是红色的外,其他一模一样,这正是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女人,我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。我死死盯着墙上的油画,心生寒意,只觉得那女人突然嘴角上扬,朝我笑了一下,我吓得哇一声,又哭了。母亲赶忙跑过来看我,急切地问道,“又怎么了呀?”我哭着指着那副油画,“昨晚,就是——那个——女人”。母亲还是不相信我说的,说那是港台某女歌星。
直到有一天晚上,母亲又去值班了,我一个人在家睡觉。耳边再次传来那熟悉歌声,我睁开眼,从床上坐了起来,想看看到底是不是在做梦。在月光的照射下,屋内明亮,一切陈设清晰可见,我看着那张油画,那悠扬的歌声越来越近——突然,一个黑影从油画里缓缓散出,在半空聚成人形,越来越清晰,又是那张脸、那个女人——“嗖”的一声,那女人狞笑着,张牙舞爪,朝我飘来,向我吐出黑气,顿时我全身发冷、四肢无力,大声哭了起来。母亲听到哭声回来,我说这次看清了,上次的那个女人是从油画里出来的,她还是不信,哄我睡着,又去值班了。
第二天早上,母亲叫我起来吃饭,却怎么也叫不醒我,摸了下我的额头,很烫。一测体温,40度,吓哭了。她赶忙叫来卫生院的同事,去取了药,碾成份,用勺子冲水喂我服了药,许久还不见好转,又打了一针,人还是糊里糊涂的,只是哼了几声。折腾了一上午。到下午,还是高烧不退,她用热毛巾敷在我额头上,又托她乡镇府的同学吴生林骑摩托车去找父亲了。
父亲闻讯后,赶忙和吴生林坐着摩托车回来。母亲哭着说了我的情况后,埋怨着父亲整天忙着工作,不管我们。还对父亲说了我一直提到过的那个女人——父亲唉声叹气地说:“唉,咱家狗娃,怕是撞上了。”母亲焦急地问道:“撞上什么了?”父亲大声回道:“撞邪了!”母亲抽泣地问道:“那可怎么办呐?”父亲说:“我和林生去找邻乡的张老先生,你先照看好狗娃。”
他们到邻乡街上打听到张老先生住处,他家住在乡郊南边果园旁的一处土胚宅院,进屋后,未等说明来意,张老先生便先开口了,说:“你娃撞邪了!”再掐指一算,“是个女鬼,就附在你家墙上。”父亲和吴叔目瞪口呆惊叹道:“太神了,我们还都没开口呢,你都知道我家在卫生院?”张老先生冷笑道:“我还知道你的房子恰好是个聚阴之地,这女鬼长期受阴气滋养,如不及时除掉,恐怕后患无穷——”说罢,他拿出黄纸,用毛笔点上调好的朱砂,嘴里一边念着咒,手中的毛笔一边急促地书写,用笔行云流水,符咒一气呵成。紧接着,又画好一道符,和刚才的符略有不同。最后,他又画了第三道符,和刚才那两道就完全不同了,就连念的咒都不一样了。张老先生嘱咐父亲说,“这三道符,第一道符用红布包住,让你娃今晚带上,明天早上烧掉;第二道符也用红布包了,让娃从明天后一直戴上,要坚持戴够三个月;第三道符明天早上贴到屋内门上。”张老先生交待完后,说你们回吧。父亲急忙说,“我们是专程来请先生您为我家犬子瞧病的,请您跟我们一起回吧。”老先生说,“你们先回,我晚上去你们家,你们回去要让娃先把第一道符戴上。”父亲连忙掏出五元钱塞到老先生手里,他又塞了回去说:“你娃和我有缘呐,这钱我不能收,你拿回去!要不然我不敢给你娃看哩。”他们谢过老先生后,便匆匆赶回家。一进家门,便吩咐母亲用红布把第一道符包起来,用红线扎住,给我戴到脖子上——母亲着急地问:“那先生怎么没来呢?”父亲平静地回答,“他晚上来”。母亲做了晚饭,吃过饭后,父亲让吴叔回家休息,觉得劳烦了他一天不好意思,吴叔表示都是老同学了,小事一桩。还叮咛说晚上要有啥事就去找他。说罢,他骑上摩托回家了。
父亲和母亲一直等到凌晨十二点多,也没有等到张老先生来。就让母亲先和我睡觉,我这时略有好转,额头还是很烫,还在熟睡中。大概凌晨一点左右,父亲听到外面有敲门声,一开门,喵——喵——喵——一只黑猫冲了进来。父亲生气极了,骂骂咧咧地拿起床头的扫帚追打黑猫,那黑猫身形矫健,一跃飞到窗台上,父亲打不上,只见它眼睛死死地盯着墙上的那副油画,喵的一声,纵身跃向油画,一爪下去,愣是将油画撕了个大窟窿,那女人的整张脸都被撕掉了。父亲怒而大骂,“你这畜生!赶紧滚!”一扫帚扔到黑猫背上,那猫一声惨叫,从墙上掉落,快速地用身体攉开门缝逃走了。屋内留下父亲一个人抽着烟,大概等到三点多,母亲起来摸了摸我的额头,已经不烫了。这时,我醒来了,口干舌燥,要喝水,父亲赶忙倒了杯水,又拿了一个空杯子,两个杯子来回倒水,尝了一口,觉得不烫,就端过去让母亲给我喝。我大口大口地喝完水后,竟开口和父母说话了,父亲过去又摸了下我的额头,不烫了。吩咐母亲为我测体温,五分钟后,拿出来一看,36度多。他激动地说,“太好了!狗娃好了!”母亲埋怨道,“都说张老先生本事大,今晚人都没来呢。”父亲气得对母亲说,“都说他道行高深,从不失信于人,这次居然没来。我明天定要去他家看看是什么情况。”母亲说,“狗娃都好了,算了吧。”父亲说:“我明天定要问出个究竟。”
第二天,一大早父亲就和吴叔去找张老先生了。到老先生家后,他老伴说老先生背疼,在炕上躺着。父亲气冲冲地走进屋子,质问他为什么不守信。老先生说:“你这人真可憎!我给你娃看病,你还打我。”父亲一脸无辜地说,“你都没来,我怎么打你了?”他说,“那只黑猫就是我。”父亲怒斥道,“胡说!黑猫怎么可能是你?不要狡辩!”张老先生让父亲从他背后揭开衣服一看,后背足有拳头大的瘀青。父亲用手一按,“哎呀,别按!很疼。你打我的时候还骂我是畜生!还让我滚!”父亲看过他后背的伤,再回想起昨晚自己确实是这么骂那只猫的,顿时一惊,悔恨地对他说,“真的是您呀!我真是对不起您!都怪我,眼窝让猪油糊住了!不仅打了您,还冤枉您。”说罢,掏出十元钱死活要给老先生,让他买点跌打药。在二人的相互推扯中,父亲硬是把钱塞进了他的被窝里,急急忙忙道了个歉,就和吴叔回去了。
他们回去后,母亲已经烧了那副油画和第一道护身符,给我戴了第二道护身符,又给门上贴了第三道符。从那以后,我就再也没见到那个女人了。乡亲们都说张老先生的道行高深,白天画符给人看病,晚上化作黑猫捉鬼除魅。
相关阅读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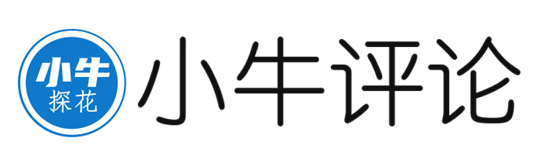

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